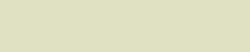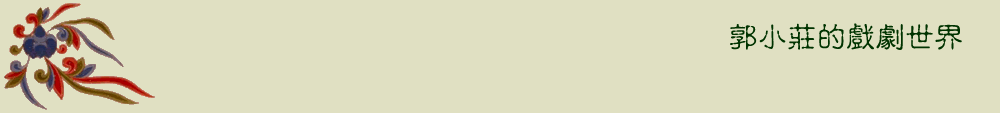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試看「王魁負桂英」─俞大綱教授遺作 台灣京戲劇一向保存傳統表演方式,至今仍有撿場、平光照明,極少例外。郭小莊的「雅音小集」大膽闖新,招徠年輕的觀眾,為垂垂老去的國劇注入新鮮的血液。 郭小莊及她的「雅音小集」將於十月廿四、廿五、廿六、廿七,參加亞洲藝術節演出四天,貼出的戲碼「王魁負桂英」一劇,由已故俞大綱先生特為小莊而寫,筆者曾受教於俞先生,試著分析此劇,追念老師。 (一)採取西方的編劇方法 京劇的生長,以至開花結果,泰半都是在一種自生自長的情況底下,文人鄙視京劇文詞粗俗、泥土味太重,不願參與編劇,只好讓伶人一手包辦整個戲劇王國。 伶人多半只求藝的精進,往往偏於技術的訓練,力求唱工、做工的漂亮,對於劇本自身散漫的結構、甚至荒謬的劇情、違背常理都不注意,從不加以刪修、重新組織、往往連戲詞都不通順,更談不上是否注意到它的戲劇條件。 以倫理意識為主題的京劇,故事來源,雖承襲了一部份較早的戲劇,如宋元南戲、元雜劇、明傳奇的題材,但依據民間傳說和演義小說改編成戲的,更是京戲劇本主要的來源,如「三國演義」、「楊家將」、「水滸傳」、「西遊記」等。 後台老伶工將小說改編成戲時,並不瞭解戲劇與小說實質上的差異,只照章回小說形式,以平舖直敘說故事的方法,將小說的人物借舞台活化起來,至於情節的起承轉合,人物心理的刻劃,極少考慮。 文人參與編劇,是在極晚近的時候,一直到京劇受人力、時間以及其他客觀因素的琢磨,已經相當成熟而被文人肯定它的藝術價值時,才開始有文藝人士圍繞在名伶梅蘭芳等左右,幫他修改舊本子不合理的地方,或者舊事新編。 戲劇理論家俞大綱先生,雅好皮簧、昆腔,研究著書之餘,手癢編寫了三個文人戲:「王魁負桂英」、「新繡襦記」、「楊八妹」為中國京劇展開了一個新境界。 「王魁負桂英」的本子,是依據宋元南戲佚文、明王玉峰的「焚香記」及川劇「情探」編寫而成。 劇作者俞大綱先生顯然意識到,如果這一代的中國人還因襲傳統編劇的老路,不在劇本上下功夫,那麼京戲這劇種,無疑地會很快沒落,賸下這套精采絕倫的表演方法,終究不過是死的。 俞先生珍惜京戲的表演形式,把「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」的規範當成京戲的特質,他為我們寫出了與現代人的感情可以交通的「王魁負桂英」,俞先生採取了西方的──或者說比較合理的──編劇方法,把京戲劇本所習見的枝葉橫生、漫無組織的情節,一一鏟除,而致用一種深入劇中人心理的、感覺細膩的手法來編寫。 此劇以結構而論,符合「單一情節」的原則,作者把整個戲濃縮到一個主幹,所有戲裡的發展、危機、衝突、高潮,甚至結尾,都依附這主幹進行。俞先生把戲的焦點集中於桂英身上──他所最喜愛的人物,我們可以說這是個焦桂英的戲。 全劇是由六場戲所串連而成,第一場寄書,等於是序曲,「訣院」托出了桂英的性格與決心,「淒控」與「冥路」兩場戲都是為最後高潮的準備,可以說「王魁負桂英」的戲劇動作是始於桂英的期待,接下來懸樑自盡,最後找到王魁,令這負心人誤傷自己。 全劇的過程離不開這軌跡,除了這條「外在情節」(PHYSICAL PLOT),還有更重要的「心理情節」,也就是主人翁焦桂英心理活動的情形:由她執著的痴情,發展到被王魁遺棄後的悲憤,然後又不死心地去探情,這一連串心理的起伏,我們稱之為「心理情節」。 俞先生在此劇中,巧妙地把兩條有形與無形的情節線索綁在一起,另外兩個主要人物王魁、王興,也向著同一方向,造成相輔相成的效果,如此,「王魁負桂英」就成了有跡可尋,結構緊湊的一齣戲了。 (二)精神層次的真情與人世間權勢的衝突 俞先生揚棄了京戲習見的大堆頭,卻又因角色太多而成累贅的陋習,他以最經濟的手法,把戲放在三個人物身上:桂英、王魁、王興,這三個人都有存在的理由,運用他們之間的衝突矛盾來推動情節的發展,這種凌驚習見京戲劇本的編寫方法,顯示出俞先生深懂京戲的上詩的美感,他在劇本中強調詩劇的單純美感。 主題則是古老又常新的:屬於精神層次的真情與人世間權勢的衝突,在戲裡,白髮飄飄的老僕王興,以及青樓女子焦桂英,合力呼喊出人類的摯情,以及對索求應有公道的努力,卻因為他們的微賤,而令他們的呼喊,只不過成了一個淒涼的手勢,也因為這,全劇充滿了悲劇的氛圍。 王魁是個不顧情義一味往上爬的勢利的小人,飽讀詩書只不過是做為他得權得勢的手段,這個往後應該以身訓人的「狀元公」,他的絕情,比起青樓女子焦桂英的痴情,以及對情感的維護,是何等辛辣的嘲諷,劇作者除了運用「對比」產生戲劇上的嘲弄外,也同時點出他對桂英人格的尊重,這是何等的胸襟。 然而,俞先生太重視焦桂英所提出的精神價值──對人世間真情的渴求,也因為作者太厚道了,一心想要替被侮辱、被傷殘的弱者伸冤,他的這片心意籠罩全劇,也因此把王魁醜化了,劇作者沒把王魁的苦衷、心情挖深進去,也沒能為王魁週遭的矛盾,設身處地的想一想,使得王魁這一角色的刻劃只留於浮面,未能深入探看王魁內心的糾葛,顯出了人物二分法的痕跡。 這樣的處理,使得王魁與焦桂英的關係不能平衡,削弱了兩人互相爭持的力量,戲的張力稍嫌不夠。這種一面倒的形象,還是出於劇作者太過厚道,他實在無法忍受王魁的薄倖,以致只強調王魁負心人格上的缺點,卻不願顧及到王魁的苦楚。 最明顯的,是在王魁知道桂英殉情,接下去「情探」一場,他去書齋小坐片刻,為的是「定一定神思,以免相府千金,被她看破我的心事」,還狠心自得地吟哦「落花如有恨,墜地也無聲」。 相反地,被逼死的桂英還淒惋地前來乞求這負心人,替他留餘地,以中國女性那種還可以原諒的寬容心懷,試圖拾回昔日的恩愛。 王魁這時充分顯出了他的知識的、地位貴族的優越感,受制於劇作者爭著公道的聲討聲中,觀眾除了氣憤顯然被故意醜化的王魁,而感動於桂英為愛而死的絕烈勇氣之外,一點動彈餘地都沒有。 (三)情探──焦桂英來索取公道 最後一場戲,桂英的靈魂來找王魁,就俞先生的解釋,完全是王魁自己一連串的精神活動,這場戲所發生的一切完全是從王魁的眼睛所看到的,因之,桂英的鬼魂出現,就俞先生的解釋,和傳統京戲中,利用神鬼來報復的意義,則有不同之處,他並不借用「女鬼索命」的俗套,「情探」一場,桂英卸下鬼扮,以原來面目出現,俞先生把桂英拉到人間來,這一個安排很重要,唯有如此,兩人之間的愛恨、糾葛,以及心理的翻騰才是可信的,桂英以一生命之軀,向王魁淒求,才更有真實美感而且有力。 如果換上陰陽兩個世界,桂英來討取公道,試探真情的動機就顯得虛飄而荒誕了。俞先生肯定了人的力量,而不假借神鬼超自然之力,這種態度誠然值得尊敬。 劇作家俞先生明白戲劇是一種「視覺藝術」,由演員外面形象的動作擊入觀眾心裡,感動力往往比語言的力量要大,表現桂英刻骨的相思,也運用了兩個動作來顯現: 一是桂英倚門而望的動作,另一個是她把筆、硯、書排好,自己坐在一旁,裝做陪王魁讀書,另外俞先生把羅帕這一「道具」用得極好,它可以是代表愛情的信物,也可以用來做自殺的工具。 郭小莊的焦桂英有超水準的演出,當年以一個入世未深的少女,她卻能掌握焦桂英的心情,以及好幾個心理變化,過程可信,層次分明。 尤其是「看信」一景,短短時間內,郭小莊捕捉了幾個全然不同的感受:先是甜蜜、轉為驚詫、再是絕望,最後決定以身殉情,心理的轉折刻劃極為深入。 京戲表演做工來看,郭小莊「冥路」一場,上吊海神廟的桂英背著身出場,幾個碎步,猛然一轉身,這一亮相,充滿了無比戲劇性,女鬼僵直著身軀,眼珠定定的,眨也不眨,兩隻長長的袖子垂了下來,幾乎觸地。 桂英走著魂子步跑圓場,沒有生命的軀體,腳不著地似的,忽高忽低,隨風飄來盪去,猶如行走在雲霧之上,突然,她長袖一揮,冥府的陰氣彷彿滲入劇院每一個角落…… 郭小莊的鬼扮身段,舞台上的魂子步,簡直可以將它從戲劇中抽離出來,獨立成為純粹的舞蹈,而之所以達到這種效果,全在於郭小莊功底深厚,平日苦練的結果。 筆者認為京戲最美的一剎那,是台上一陣舞動之中,催鼓驟然止住,演員擺出最好看的架式,凝固「亮相」(POSE),此時的姿勢最具雕塑美感,是藝術形象的湧現,「冥路」中的女鬼,凝止的剎那,真是淒絕美絕。 「王魁負桂英」是個充滿了文人氣息的劇作──其中好詞充塞,單線進行的情節不免使全劇略嫌單薄,可喜的是裡面有俞先生深厚的同情心與縱橫的氣勢做支撐,它是一齣風格特出、純淨淒美的好戲。 筆者為俞大綱先生的學生,在他去世後十一年,能夠在此間看到俞先生在世時寄予厚望的京劇旦角郭小莊,帶著她的「雅音小集」前來香江敷演老師名作,心中感慨良多,人世間的滄桑莫過於此,可幸老師的詩文口白終將延續下去,繞樑不絕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