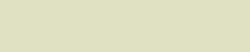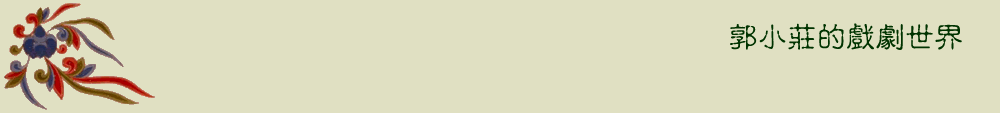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我似乎嫁給了他 ●我是愛漂亮的。初入劇校時原被分派到小生組,我勇氣十足地向老師說:「我要學花旦,不要學小生!」老師好奇地問為什麼,我理直氣壯地說:「女生可以戴花,男生又不能戴花!」就這樣我順利成為旦角組的第十名學生。 委屈扮宮女 被人嫌醜 那段跑龍套的日子總算沒有白跑,我常常在想:從舞台邊緣的龍套位置,讓我更深刻地去領會戲的內涵,並成為戲劇表演的沃土。 演出扈三娘 一炮而紅 那晚演的是重頭戲「扈三娘」,鑼鼓聲起,我一顆心小鹿似地亂撞,一出場祇見全場滿座,台前鎂光燈亂閃,正唱著舞著,突然聽見後排觀眾鼓譟,心一慌想道:「完了,有人喝倒采!」也不知怎麼唱完這場戲的,進了後台才知道原來觀眾不是喝倒采,而是抗議前面的攝影師擋住了視線。 「扈三娘」為我扭轉了在劇團的地位,我一個月領三百八十元薪水,銅山街的寢室也變成了單人房,生活從刻刻板板的團體生活逐漸擁有個人空間。 十七歲那年,我搬回家住,卻又對家庭生活產生「不適症」,父親重新訓練我遵守生活禮儀,我常常以不講話來表示抗議。然而,父親在客廳裝上大面鏡子,作為我的排練室,並請朱少龍老師隨時來給我吊嗓子,仍然以我的國劇生命作為這個家的優先選擇。 恩師俞大綱 啟迪良多 在俞老師「不要有師承之限」的教誨下,我廣泛吸收各家之長,跟李湘芬老師學梅派戲,又從顧正秋老師學「玉獅墜」等戲,還有馬述賢老師的「紅娘」、梁秀娟老師的「思凡」等。 俞老師為我編寫的「王魁負桂英」,更讓我跨出旦角戲之限,開始演出青衣、花旦戲;於是也不再有人以「郭小莊哭也像笑」來取笑我不能演青衣戲!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