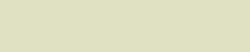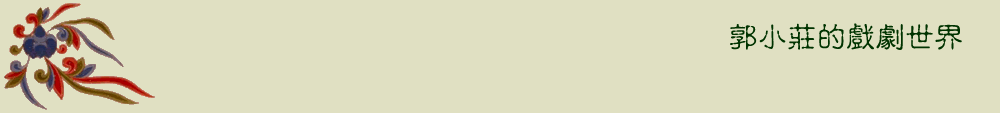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弟弟: 俞大綱教授猝以心臟病過世,到今天剛好一個月,她的姐姐俞大綵女士寫了這篇至性至情的文章。俞女士因為過度傷感,曾進入榮民總醫院休養了七天。--編者 弟弟,你為甚麼如此突然的不辭而別,形單影隻,悄悄的走向另一個世界,一去不反? 僅僅四個月前,我拿著剛寫完的「憶孟真」文稿,到大綱家給他看,想在文章發表之前,徵求他的意見和得到他的批評。 他穿著一套舊睡衣,從書房走到客室,坐在一張搖椅上,在一盞昏暗的台燈光下,仔細閱讀;我突然感覺到他有老態,很像我們晚年多病的父親──父親也只活到六十八歲。 過了一段沉寂的時刻,我問他的意見,他啞著嗓子說:「寫得好嘛。」接著,雙手掩面涕泣,哽咽著說:「姐夫死得太早了!」 大綱患有先天性心臟擴大症,感情不宜過於激動。我不敢在他面前流淚,沒有留下來吃晚餐,便起身辭去。臨行時,他淚痕未乾,輕輕拍著我的肩膀說:「我勸你,更希望你,以後多寫文章。」 是的,依照他的願望,今夜,我又在嘗試寫作了。但萬萬料不到,我要寫的竟是一篇哀悼我最親近,最疼愛的弟弟的文字! 廊外夜來香的芬芳,在晚風中一陣陣的透入紗窗,一對金絲鳥縮著脖子在籠中並肩安息。我居處簡陋,在此室中,我常跟大綱說笑,我說,用『斯是陋室』來形容我的家,很合適,但下半句,我便不配引來自誇了。他卻極為欣賞我家鳥語花香的氣氛。 好寂靜的夜!小香爐中三柱檀香,輕煙裊裊上升。我淚眼模糊,彷彿又看見弟弟清秀的面容,聽到他低沉的聲音,輕喚一聲「懷姐」。我禁不住失聲痛哭。窗外有細雨聲,如泣如訴,使我幾度擱筆,不能成書。 我們在上海長大,家中兄弟姊妹眾多。大維居長,大綱最幼,排行第八,兄姐們叫他「小八」。我長大綱一歲,是幼女,小名「懷細」,兄姐們叫我「小懷」,大綱稱我「懷姐」。 我倆從小一起長大,直到十四五歲,分別住入男女學校,可以說是形影不離。在我的記憶中,我們自幼不曾爭吵過一句,遇事總是互相禮讓,愛聽母親為我們講「融四歲,能讓梨」一類的故事。稍長,更加友愛,從中年直到「從心所欲」之年,尤增互相關切。他關懷我的勞累,貧困,獨居的生活,我則不僅關懷,更加憂慮,他多年的心臟病。我深感內疚與遺憾的,是近幾年來,我除勸他多注意自己的健康外,不曾盡力強迫他做每年例行的健康檢查。現在後悔已太晚了。說甚麼後悔,內疚,遺憾,弟弟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。 而他對我呢,多年前他對我一切關懷的「古」事,暫且不談(去年在他的學生歡宴他的餐會上,他曾笑著自喻為老古董)。 幾年前,我忽然收到大綱用掛號信寄來台幣四千元支票一張。當夜來電話,說他所得到的四萬元文藝獎金他希望我分享一部份,買些愛吃的和欣賞的花草等等。他不敢親自送來,因為他深知我的「古怪」脾氣,一定不肯接受。他笑著說:「我送來,遭你當面『原物退還』(平劇樊江關劇詞)豈不傷了老姊弟的和氣?」我桌上,小几上,擺設的一些小巧玲瓏的陶器,小磁觀音,木刻聖母像等物,都是他物色到,買來送給我的。如今,睹物思人,倍增悲戚。 連夜不能成眠,伏案小睡,矇矓中走入童年時優遊嬉樂的世界。父母親非常注重兒女的教育,長兄大維出國深造時,大綱與我才十一二歲,其他諸兄姐們,到十二三歲,均被送入學校住讀。因大綱與我最幼,留在家中,延師先讀國文,另有一位陳女士教英算。來我們家寄讀國文的有譚季甫(現任台灣造船公司董事長)譚韻(陳冠澄夫人,現在美國),他們是譚祖庵先生的幼兒幼女,陳辭修夫人譚祥女士的幼弟幼妹。我們四人,朝暮相處,情同手足。 大綱於民國四十八年譔並書「譚季甫伉儷五十雙壽敘」第一段說:先嚴君與茶陵譚畏公昆季綺歲定交,久而彌篤,晚共搆廬於上海塘山路,蹤跡益密,文酒之會月無數日曠,畏公有事於粵海,以家事重屬先君,並遣季甫偕其弱妹韻寄讀於余家東塾,與余姊大綵同受業於衡陽胡舜欽師,溯洄往日,垂四十年矣。」 我們的國文先生,(當時不稱老師而稱先生)湖南衡陽人,姓胡,那時年已過六十,學問好,教導極嚴,但慈祥和藹。我們作文寫得好,詩詞背得熟,老先生便買糖果給我們吃。 我們輪流被叫起來背書,起立背向先生,背著雙手,身體左右搖擺,朗朗背誦唐詩、宋詞,六朝文賦等等。常常到下午放學前十多分鐘,趁先生閉目養神時,大綱與我相約高聲背誦,把先生驚醒,即告知放學的時間已到,便飛奔到園中頑耍去了。 「將軍一去,大樹彫零;壯士不還,寒風蕭瑟。……」弟弟幼童清脆可愛的嗓子,好像又湧到我耳邊,我又好像看見他瘦弱的身體,左右大搖大擺。這一切不是昨日的事麼! 父親性愛花,家中培養的蘭花菊花,不下數百盆,東籬採菊,幽室賞蘭,是父親的一大享受。而我們卻與譚氏兄妹,把空花盆倒撲在園中地上,築成一條「盆路」,興高采烈的踩在盆上奔走,踏破無數花盆。 有一次,親戚家送來一對羽毛潔白的仙鶴。母親酷愛看書吟詩,但興之所至,偶而小立窗前,觀看白鶴漫步於青草上。記得有一天,忽下大雨,園中積水盈尺,大綱與我赤著腳,捲起褲管,在水中前後花園追逐雙鳥為樂。鶴驚恐,高飛越籬而過,不知飛向何方去了。 我擔心要挨責罵。大綱卻站在水中,仰望天空說:「『白』鶴一去不復反了!」那一次我們未遭責罵,必是父母親嘉許我們有「放生」之德? 另一次,大綱與我在父親書齋中,拿了十餘張上好的高麗紙,裁成橫直條,寫上我們認為是自己的傑作;幼稚的詩,詞,對聯,掛滿後園竹亭,適值父親自外歸來,令我們立刻撕去,怒罵我們說,不得許可而擅自拿別人的東西,是為偷竊。我們因受責而慚愧,因觸怒父親而傷心,小小的心靈竟大感不安,相對痛哭。 這一切都是五十餘年前的事了,往事依稀,而今日,弟弟卻獨自乘鶴而去,不復反矣! 大綱資質聰穎,天才橫溢.他不但博覽群書,本身便是一部活書。一部有生命,有靈性,有感情的書,因為他過的是充滿感情,給人溫暖的生活,尤其在他生命最後幾年中,已達到「無我」的境界。 弟妹鄧敬行女士,近幾年內,兩次因血壓過高,半身不遂,住醫院就診,大綱日夜陪伴在側,食無定時,睡不安蓆,勞累焦急。果不出我所料,他又需要吸氧氣來止心痛了。我可憐他,更恨他,太不自私了。 他愛才,對青年學生們鼓勵提攜,不遺餘力,諄諄導誘,教誨不倦。狹窄的辦公室,變成講堂,擠滿了學生,往往深夜在電話中跟學生討論文藝;這是他的生活。 他去世後,學生們痛哭哀悼;在善導寺後屋向他的遺骸,在追思會中向他的遺像,跪拜涕泣,這是青年們感情的流露。他遺下他們不顧,而獨自離去,太使他們傷心了。 弟弟的聲音從電話中傳過來,那是他去世前幾天的事,也是我們最後一次的電話交談。他說,有幾小盆花,不是如往常一樣要送給我,而是要自己留著,他要開始學習培養盆花了。我聽了非常高興,告訴他說,養花可以調劑他的生活,花襯著他滿屋的書。豈不更雅?當天日落後,我選出三隻顏色素淡,花紋典雅的小花盆,插入花秧準備三五日後送去,給他一次意想不到的驚喜。我每日清晨起床,除蟲澆水。如今,嫩芽已長數寸,但弟弟卻永遠不會回家了!還說甚麼書香盈室,花氣襲人? 我們兩人,都習慣晚睡,午夜電話中常傳來一聲「懷姐!我是小八」。然後,滔滔不絕,天南地北,無所不談,他似乎老有說不完的話。 但三個月前,我因身體不適,住榮民醫院數日。出院後雖已痊癒,但深夜電話中,他不再討論音樂、文藝;如文藝中心某一闋戲,陳若曦的新作,馬友友扣人心弦的大提琴演奏會等等,而是喋喋不休的要我保重身體,如右眼有白內障,不宜多看書,因胸部作痛等病,要我戒煙,要我在應酬場合上少喝酒;少操勞,多做健身運動之類的話。關切之情,溢於言表。在電話這邊的我,不知其所以然的,流下淚來。他又比我們為用得太久,太舊的鐘錶,機件失靈,想要多用幾年,非得時常注意修理不可了。 言猶在耳,孰料他自己這座破舊的鐘,突如其來的停止擺動,要修理也來不及了。他的突然逝世,留給八十高齡的長兄大維與我,無盡的懷念與追思。 讀陳怡真本月十三日登載在中國時報的「立雪再生來」一文,感觸太深。誠如她說的,大綱把他的辦公室比作破廟,他自己便是破廟中的老和尚。「如今破廟尚存,卻永遠看不見那可愛的老和尚了。」 我改不了遲眠的習慣,電話機安然坐在書架上,我卻永遠聽不見深夜電話中傳來「懷姐,我是小八」的聲音了。 本年二月十九日,大綱給譚韻的最後一封信說:「你把世事看得太認真。我們生在這個大變動時代,能苟活到六七十歲,已屬萬幸。我與八嫂已無後顧之憂。兒女均已長大成家,心願早已了了,已無何留戀與放心不下之處。……」 他無痛苦的離去,得到永久的,安靜的休息,在他本人是超脫了,卻把悲悼與追思,留給一群愛他的人。 死別吞聲,我不敢希望弟弟能入我夢,解我的長相憶。室中我為他點的三炷香,已化成灰,我卻有流不乾的淚水。 --六十六年五月廿八日於台北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