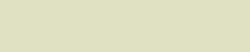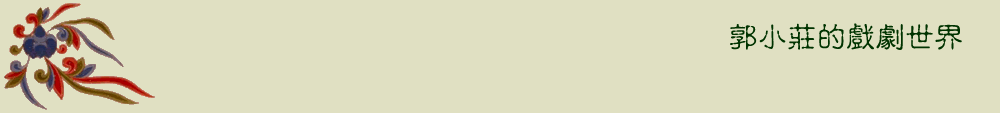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出自中國的土壤 談起平劇未來的發展,我不喜歡用「改良」這一詞彙,因為過去的不一定「不良」,而新改的則不一定「良」;我寧可用「創新」這個詞語,蓋「新」者總是以前所未出現過的,或多或少帶有原創性的意味。平劇能否容許我們創新?那些方面容許我們創新?此乃本文所要提出來討論的問題。 平劇能否容許我們創新,我以為這是一個觀念的問題。如果你認為平劇是國粹,必要原樣的保存,就像我們保存古代的文物和古蹟那樣,一絲一毫都不能改變。在此一觀念之下,自不發生創新的問題。但是平劇卻成為死的劇種,只能供人憑弔,發思古令幽情;只是表示我們的祖先曾經創造過這樣的一種戲劇模式,而與我們現代人生並不相干。反之,如果你認為平劇仍是活的藝術,不僅是活在舞台上,而且活在我們的意識形態裏,與我們呼吸相通,血脈相連,仍然為我們大家所喜愛。在此一觀念之下,才會發生創新的問題。所謂創新,自年輕一代的觀眾言,他們希望見到所能理解、所可接受和滿足他們趣味的,或者說能反映現代精神的作品,平劇的劇本自需注入新的內涵。自平劇的演出者言,如不自甘為一個模擬者,而要把自己提升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,那就總希望走出前人的窠臼,自闢蹊徑,也就是如何在形式上,或表現方法上突破前人。平劇的演出自會出現新的樣式。 在上述兩種觀念裏,我贊成後者。我認為平劇的成長不過二百餘年,在抗戰之前仍然是它的盛期。其衰落是近三、四十年之事;即使如此,在台北市仍然經常維持它的演出,而且有新的劇本產生;尤有進者,它那套完整的表現方法已受到世界人士之注意,研究的人正不斷的增加。因此我們絕不能把它作為古董來看待,這一筆先人的遺產,應該在我們以及我們未來子孫的手中,發揚光大,所以我們應該保持它的活潑的創造性。 自此一認知的基礎,我願一抒己見。 先談劇本,平劇的劇本的出現,自整個世界的劇壇言,是相當晚近之事。遠者如希臘戲劇,距今已二千五百餘年,現代人讀來,仍然是氣象萬千,感人至深。近者如莎士比亞,亦有三百餘年歷史。不久前我在電視機前,觀賞「凱撒大帝」的影片,那股懾人力量,使我思潮起伏,久久不能自已。此類劇本絕不因時代的變遷而失去其價值。為什麼此種劇本能傳之久遠,而別的則不能呢?我借用亞里士多德的觀念來加以說明。因為它所描述的「不是已發生之事,而是一種可能發生之事;此種可能性乃指某一性質之人將蓋然的或必然的說或做某種之事」(1)。也就是說,劇中人具備人類的某種基本性格,此種性格的人在古代會做出某種事來,在今天亦可能做出某種事來;這種人便不是抽象的人,而是生活在我們中間,甚至我們自己的身上,我們當然會對他產生共感。 同時,此種人物是複雜的,而非單純的概念化的人物。例如上述「凱撒大帝」中的布魯塔斯(Brutus)與安東尼,你能用簡單的語言來描述他們嗎?事實上給予人們的感受是因人而異的,如果用當代符號學(Semiotics)的觀念來說明;我們自舞台上所見及的語言、動作和各種「符號工具」(Sign-Vehicle)所傳達出來的「表現」、「內容」,以及其相關意義,乃是它的「外延」(Denotation),屬第一層次的意義。當所有這些(即外延)結合起來又形成另一符號,即Bogatyrev所謂「符號之符號」(Signs of Signs)(2),而產生新的符旨(Signified),斯為第二層次的意義,稱之為「內包」(Connotation)。「內包」係與文化層面相關,可能涉及到社會學、人類學、心理學等各種知識範圍,所以是多義的,不同的人會得出不同的意義。西方的偉大戲劇必包含「外延」與「內包」兩個層面的意義,形成意義的複雜化,不同的時代,不同的個人,可以用自身的文化條件來豐富它。 我國平劇的劇本則非出自大文學家之手,而係來自民間,故遠為通俗易解,劇中人物非常單純,顯得善惡分明,忠奸立判。此種人物屬於意念化的人物,所代表的為忠、孝、節、義之類善的觀念,或奸、佞、貪、鄙之類惡的觀念,其餘的成分則被抽取一空,而成為某一觀念的化身; 他們的語言、動作和各種「符號工具」(如服裝、臉譜)所傳達出來的「表現」、「內容」以及其相關意義,鮮明突出,一目了然,不可能產生歧義。故Keir Elam 認為:「在中國的古典劇場與日本的能劇場中,其語意單位係如此嚴格地被預定了,使外延與內包之區別實際消失:所有的意義均是初級的和相當的明確。」(3),真是一針見血之論。 一部戲劇若係自人類天性出發,其可能不受時代地域的限制;而一部自特定觀念出發的戲劇,則必受時代地域的限制。我們知道平劇興起於清代中葉,與今日的台灣相比較,其社會結構、時代特性,無論自實質到精神,都迥然有別,前者是專制帝王的時代,農業社會的結構;而後者是民主平等的現代,是工商業社會的結構,不同的時代、社會,自必產生不同的道德觀、不同的文化特質和不同的意識形態。於是在當時許多視為當然的觀念,在今日年輕的一代人中已無法體認。是故我們要創作新的戲劇,勢必要擺脫那些陳舊了的觀念,而向那些超時代、超地域的人類天性中去發掘。我國是一個文明古國,一部二十五史就有取之不盡,用之不竭的題材,再加上流行於民間的神話、傳說,足以傲視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。作為一個作家,生在中國應該是最大的幸福!但是我要聲明的,我所謂的超時代、超地域的故事,並非自虛空中建造起來的,它仍然是出自中國的土壤,具有中華民族的特色的;問題是在這特殊文化背景的事件中應蘊含一般性或恒常性,使觀眾所感悟的不是一個陳舊的觀念,而是真正中華民族的精神特質。因此我認為在平劇的創作上仍然有一個廣大的世界供我們去展現,去開拓。 同時平劇是融合了音樂、舞蹈和特技的表演藝術,劇本只是它的一環;有了好的劇本並不表示有了好的舞台藝術,因此必要進一步探討它的表演性的問題。 事實上,平劇的表演性才是它的靈魂。例如「問樵」(瓊林宴之一折)所描寫的乃范仲禹因妻兒散失,四處打探,途中遇一樵夫,乃向其探詢妻兒下落。情節可以說簡到不能再簡,可是在舞台上所見到的,身段之繁複,把一個精神失常人之形態,表露無遺。又如「掃松下書」,描述張廣才祭掃蔡家二老墳墓,與一為蔡伯喈送信使者相值,張廣才乃借機痛斥蔡伯喈之不孝,故事亦是十分單薄,雖然我無緣看到麒麟童(我在大學時代看過一次票友的演出,至今記憶猶新)的演出,但是每聽他的唱片,那種悲涼蒼勁的聲音,配合著丑角的插科打諢,使我百聽不厭。所以平劇的生命是建立在它的表演上。 所謂表演,包含唱做兩方面,在唱的方面,前輩的藝人,無不自創新腔,獨樹一幟;在做的方面,亦是如此。例如在梅蘭芳的表演生涯中,凡一字一腔,一舉手一投足,從不輕輕帶過,真個做到揣摩又揣摩,研究再研究,此種敬業精神,實在令人欽敬。我得要說,我們今天所缺乏的就是此種精神,把表演當做虛應故事,不去問為何要這樣唱,這樣做,更不會問是否還有更恰當的表現方式;最令我難過的,我曾經見到當舞台上只有兩個人時,一個正聲嘶力竭,大唱特唱的時候,而對方站在一旁,呆如木雞,彷彿與他毫不相干。這樣如何能使舞台鮮活出來? 因此我認為,雖然平劇的歷史上出現了許許多多傑出的藝人,留下了許多的規範,但不能說就止於此,就不能再越雷池一步,一個敬業的藝術家是絕不停滯的,對於他所表演的人物的性格、處境、感情,可以作更深入的探究;在唱的方面,無論是行腔、運氣、吞吐、抑揚,都可以在規矩中求變化,甚至自創新腔;在做的方面,對於任何一個細小的動作,亦必問其目的何在,給觀眾帶來何種效果,在合理與美觀的原則上予以變化。尤其是排演一部新劇,因為沒有前人的模本在,當然可以隨心所欲的來創造。但是就我所見到的,有的只是交代劇情,讓觀眾能看懂一個故事而已。因此我寧可看骨子老戲,因為老戲能把無戲變成有戲(如前述「問樵」、「掃松下書」),而新戲往往把有戲變成無戲,其差別在此。 凡藝術都是整體性的,平劇自無例外。因此如何使演員間的配合更為細緻;場次間的關係更為緊湊,動作與反應更為靈活,刪其冗長,去其糟粕,以建立起更高度的完整性,我認為必要在一個頭腦的指揮下完成,方可收事半功倍之效,假如說平劇的主排人或多或少接受一點西方導演的觀念,對於平劇的創新應該是有助益的。 是故在平劇的表演方面仍然留下一片廣大的天地,以供吾人馳騁。但是並非說此種創造性沒有限制,事實上是有其先天極限的。茲說明如次。 第一、平劇不可能演出現代人的故事。記得一九七二年我在愛荷華城,一天,有人請我看平劇電影,放映的是大陸的平劇(大陸是樣版平劇,名字已忘卻),以時裝演出。當一個人穿上現代服裝,拿把步槍,踏著台步,以花臉的嗓音唱出,頓覺全身不自在起來,痛苦之極,沒有看到一半,藉故走出,寧願冒著零度下的寒風,叫車回寓。 我們知道平劇是建立在一定的慣例(Conventions)上的。它的動作、姿勢、台步、唸白、唱腔、臉譜、服裝種種,都有一定的慣例。你要接受平劇,你就得要接受這一切慣例。假如你要否定這些慣例,那就不是平劇。當然我不反對有人去創造新的戲劇,但那必定是曠世奇才,再加上風雲際會,一般人是無能為力的,因為這些慣例是歷史的累積,已形成一個完整的系統,而且密切配合,建立起一定的欣賞距離。如今突然改為現代人的語詞和服裝,觀眾自必以現代人的生活方式來衡量它,我們會覺得它不應如此,會覺得格格不入,蓋欣賞的距離一經破壞,帶給我們的將不是享受,而是痛苦。這是平劇所受先天的限制,不是任何人所能改變的。 第二、平劇不宜用實景,我記得幾年前,有一次看電視演出的平劇(大概是「蘇小妹」吧),但見在一個花木扶疏的花園裏,一個人自月牙門踏著台步,唱了出來,當時覺得無法忍受,立即關掉。 我們知道平劇是沒有實景的,雖然也用一點道具,但那不是實物,而是符號(Semiotic unit)。例如,平劇的舞台上一擺著一張桌子,這張桌子只是一個符號,當它擺在後部不用的時候,它的符旨(Signified)是空的,我們是視之而不見;當它搬到前面使用時,它可用以代表山,或任何高地,亦可以代表朝廷、法堂、宴會等各種室內景;也就是說用在不同的場合,會填入不同符旨或內含。因而使平劇展現出一片無垠的空間,和變化萬千的世界,這正是平劇的高妙處,亦從而引起西方人士的讚美與效法。在西方那種自然主義的舞台上,充滿了道具,不僅限制了舞台的變化,也約束了觀眾的想像力,故為許多人士所詬病。是以本世紀以來,如何創造舞台空間,如何打破四面牆的限制,正是大家努力以赴的。我們祖先為我們留下這樣一座奇妙的舞台,為何反要向他們學習呢?同時,一經採用實景,我們便會和現實世界的一切來比對,結果發現二者之間不相調和,而形成欣賞距離的破壞。其理由與第一點相同,不擬再贅。這就是我反對使用實景的緣故。但是適度的運用燈光,我不反對;惟必要經過精心設計,用得不妥,於事無補。 除了上述兩端之外,平劇的任何部份都容許我們創造再創造,更新又更新。但是創新不是一件容易之事,必須具備一定的素養與才華,以及高度的勇氣,同時「新」未見得就是「好」,因此我特別冀望於社會人士的,我們對於創得好的,應該予以鼓勵與支持;對於創得不好的,亦要心平氣和來討論,讓他有再試的勇氣。如果認為過去的一切都是好的,不能動其毫髮,創新乃是大逆不道,非去之不可,那不是愛護平劇,而是扼殺它! 註釋: (1)見Aristotle之「Poetics」第九章;本人譯註之「詩學箋註」第八六頁,中華書局,五十五年版。 (2)見Detr Bogatyrev撰「Semiotics in the Folk Theatre」一文;經Ladislaw Matejka與Irwin R. Titunik輯入「Semiotics of Art: Prague School Contributions」第三三至四九頁,Cambridge, Mass, MIT Press,一九七六年版。 有關符號學之著作甚多,甚推薦Roland Barthes所著「Elements of Semiology」(英譯本:Hills and Wang紐約,一九六七年版),此書簡明扼要,頗便初學。 (3)見Keir Elam著「The Semiotics of Theatre and Drama」第一一頁,Methuen倫敦,一九八0年版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