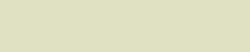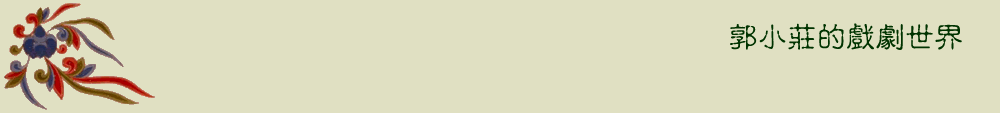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拿人生來換戲 「一朝王氣如煙散──」 穿過蟬叫聲盈耳的仁愛路行道樹,進入中廣排練室,迎面而來的是一場即將破滅的大明江山。 長平公主的「紅綾恨」正在排練。 隔著距離遠遠看去,主角隨著唱腔聲音的高低,上下顎骨在耳邊的接榫處,忽上忽下,誇張的滑動,因為瘦,看起來好像比別人多了一根骨頭。 ●有無相生 難易相成 始初,看書名「天涯相依」,並不明白,為什麼郭小莊要將這樣一本記錄自己戲劇生涯、知性多於感性的書,取名「天涯相依」?對於任何一個習慣「尋章摘句」、「望文生義」的人,「天涯相依、生死相從」八個字放在一起,無論如總意謂著幾分義無反顧的悲涼。然而,看過郭小莊,仔細讀進書裡去,才知道平劇之於她,其中何止是天涯海角、相隨相依? 「問世間情是何物,直教人生死相許」,平劇之於小莊,別人看,也許是「多了一根骨頭」,小莊自己看,則是:意願拿整個人生來換戲。 如果,「侯門一入深似海」,說的是官宦之家的「門禁森嚴」和「一去不回」,那麼,「劇門一入深似海」同樣適合用來形容郭小莊之於平劇。 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一日,一個板橋國小的二年級生,轉進大鵬劇校,開始──她的家人、她自己,甚至師長、社會、學校,都並不知道當時埋下的是一顆什麼樣的種子。而三十年後的今天,經過一萬多個日子的「磨製」,一方面,人們感嘆「歲月如梭」,一方面,人們不得不驚訝於眼前的「顏色乃見」。是的,十年來的「雅音」,和三十年來的郭小莊,都讓人進一步知道「寶劍在匣,明珠在幃,其光不能掩」並不只是虛幻的武俠形容詞。 舞台上,現實與虛幻錯綜交織的二黃唱腔,說出了長平公主避禍尼庵的一段故事── 「只說是,綵絲紅綾,花燭宴, 同樣一個長平公主,來到金庸的俠筆舞台,便是「鹿鼎記」中武藝精絕、神出鬼沒的「獨臂神尼」;來到郭小莊的平劇舞台,便是悲壯衝擊、含恨天地的「紅綾恨」──習慣拿著歷史教科書對號入座的人,看到歷史人物的改編故事,不免扼腕蹙眉。 關於被詬病「無中生有」的「改編」,郭小莊說: 「在我的理念中,人性是永遠不變的,自有應該堅持的基本原則;但藝術卻是千變萬化,沒有定制的。隨著社會的變遷,隨著個人的觀念,創作應有不同的形貌,就是這種無限的發展性,才能吸引那麼多人,窮畢生之力,澆灌藝術之花。 「歷史人物的表達方式也是不定的,表達方式若能更貼近人性,就會使其原有形貌更為深刻動人,我們又何必一一拘泥於固定的模式,抗拒新的變更或更貼近人性的闡釋呢?」 張大千曾贈言「深入傳統後,不創造怎麼叫做郭小莊?」 於是,立意創新國劇的「雅音小集」於焉成立。於是,十年來,劇目翻新、人物從歷史中活了過來──白蛇來到小莊的舞台,多了一份執著、徘徊;梁紅玉來到小莊的舞台,擂鼓聲動之外,多了一份喪子的悲懷;劉蘭芝來到小莊的舞台,同樣的佳期、盟誓、驚變、殉情,小莊的扮演,卻多了一層真情撕扯的痛苦。 ──也許,藝術真的不是在比技巧,而是比人格? ●長短相形 高下相傾 繼續看下去,當然說明了這完全是外行人的多慮──然而,罩地覆蓋的迤邐裙裾,乍看彷彿舊式女子給自己造的一個陷阱,讓自己永遠小步走路,前程有限。 趁著長平公主暫時下台,休息時的郭小莊,談起自己的角色扮演、生活起居。 「舞台上,我可能多彩多姿,生活裡,我可以說是千篇一律。多年來,我已經養成習慣,只有規律、平靜的日常生活,才能凝聚上舞台時的力量和光芒。 「我一直非常贊同俞大綱老師的一句話,他說:一個好的演員,在舞台下可能並不亮麗,因為他把所有的光都留在舞台上。我告訴自己,人不可能在舞台上、舞台下都一樣亮麗,台下用掉一份光,台上可能就少了一份亮麗。 「十年前,開始創辦雅音的時候,我已經二十七、八歲,我當時就想得很清楚:這一條路,要執著走下去,不要曇花一玩。張大千伯伯曾鼓勵我說:妳願意成為一個藝術家,還是一個演員?現在,我很清楚,我將自己定位為藝術工作者,所謂『工作者』,就是永不止息。」 對於多數人所追求的愛情、婚姻、家庭、子女,郭小莊說,自從創辦了「雅音」,使她像一個母親一樣的全心全力投入、付出。她說: 「我有豐富的感情,我的戲多半也是愛恨分明的,我在每個角色的扮演中,深入人生的喜怒哀樂,像『韓夫人』從少女扮到老婦,我從揣摩、扮演中,彷彿真實的經歷了她的一輩子。」 「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結婚,或是擁有個小孩子。我想,人生貴在自知,我知道自己是佔有欲很強的人,我表達佔有欲的方法,就是全心全意的付出。有一天,如果我結婚了,我必定也會全心全意的付出──雅音要求全心全意,家庭也要求全心全意,其中的矛盾和不能盡善盡美,都是我不能接受的。 「許多人說,現在不結婚,將來會很孤寂;但我認為,人生就是要懂得割捨,況且,愛心何必只及於自己所由出的親人?」 早年大鵬劇校的嚴格訓練,加上三十年來的持續吟唱、練功,郭小莊說自己的日常生活規律得像「軍隊一樣」──晚上一點左右睡覺,早上六點起床。她用「神經質」來形容自己的不容易熟睡──直到現在,她回憶裡很清楚的,還是大鵬劇校清晨的第一課,照著「依、烏、魚」的順序喊嗓子。 道德經裡,老子說:「知其白,守其黑,和其光,同其塵」──戲劇的眼光果真無所不在,郭小莊從平劇裡,早已習得「人生的轉移」,「知白」、「守黑」更是每一個成熟人生的必備。 ●音聲相知 前後相隨 「花燭夜竟作生死別 哀愁的確是人性中最具有感染力的感情──蕭蕭暮雨悲風緊──郭小莊躲在長平公主的裡面,泫然欲淚,纖細的手指,在水袖中撥弄著人生的千般無奈,手指忽上忽下,水袖或左或右,眼光跟隨手指一高一低,展現人生劇烈轉折,有情有節。 一場戲排下來,滿身汗水。第二度的,她開始喝水、吃藥。 「興亡夢幻早歷盡──」 在大臣的高唱聲中,郭小莊揚著濃眉看排練。不時的,她將右手大拇指、食指放在雙齒間,或輕或重的合咬著,再用左手將右手的「坦白」遮住。她說: 「並不是說要做給人家看,而是長這麼大,都快四十了,已經不是小孩子,總是要有所壓抑。有時候,覺得人生好苦,而當演員更苦。 「演員有時候必須很殘忍,什麼叫殘忍?比如,我明明很緊張,卻要表示不緊張,有時候,我覺得我對自己太殘忍──這樣壓抑下,死掉的細胞,可能比受傷流血更嚴重。」 提到成立「雅音」的「難和怕」,她說: 「要說以我一個人獨立撐持一份理想,采聲與鼓勵的背後沒有苦楚的感覺,那是太高估了自己……我清清晰晰,感覺到的苦和難只是:卸幕! 「難與怕,都只在一剎那間,但自幼至長,一齣齣戲演下來,也忍下來,卸幕卻成為意識底下一層悵悵的威脅,甚至做惡夢也會聽見忽然一聲高呼:「卸幕囉!」 相信戲劇是「一遍拆洗一遍新」,郭小莊在啟幕與落幕間,不斷扮演人生,她舉例說明其中的一個挫折: 「由於立意創新平劇,招來許多非議。『竇娥冤』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。當時演出時間、地點、門票全都安排好了,卻有人出面中傷,說是這齣戲的故事影射當時政治事件施明德,說雅音是要為施案『雪冤』,報請有關單位,禁止演出。憑著為雅音、為平劇爭生存的勇氣和毅力,我不懼一切的抗說到底,直到最後一刻,才爭取到照准如期演出。」 她承認自己很重感情,常常在角色認同過程中,為主角的掙扎和遭遇,傷心落淚,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」,尤其讓她黯然。不過,歷經十年雅音,她覺得自己的淚和汗並沒有白流。她強調: 「人生的淚水通常都是自己在控制。從前,小時候,我對著父母哭學校管教太嚴。長大後,遇到不如意的事,也都向家人傾訴。現在,我逐漸學會了控制自己,知道哭泣是一種發洩,我會躲進浴室,對著鏡子大哭一場,或者把自己關在黑暗的房裡,讓看不見的黑拭去臉上的淚。」 脫下汗濕戲服,烈日已轉為斜陽。換上家居衣服、白鞋子,因為受過平劇的嚴格訓練,她走起路來像雲,是「飄」過來的。 沒有應酬、從不逛街、極少出門,一天裡面,她曬到陽光的機會,少之又少,整個人看起來是透明的。 「我習慣在舞台上詮釋各種人生的悲喜。走下舞台後,自認是個單純的人。」 從小喜歡聽佛經的梵唱,覺得很遙遠、很安靜、很好聽。十六歲,就是一個正式皈依的佛教徒──郭小莊在同一條直線上,同時經營舞台的喧嘩和生活的平靜。 認同「人生如戲」的道理,大約不算太難,而真正從行動做起,拿人生來換戲的,大概沒有幾個人。 不曉得,「專氣致柔能嬰兒」,指的是不是像她這樣的一種專注? 這個單純的人,對平劇的鍾愛、聞雞起舞,恰如詩人筆下的二句詩── 一個堅定的信念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