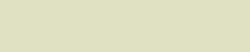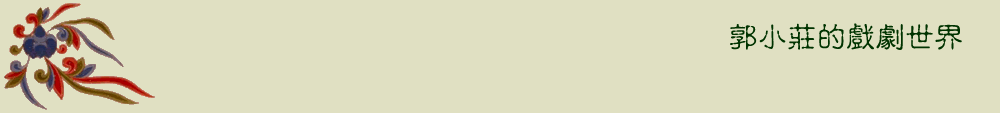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紅綾恨 民國六十八年,郭小莊女士創「雅音小集」。歲月如矢,忽焉十載。這是一段艱辛歷程,雅音小集之於國劇,與林懷民「雲門舞集」之於舞蹈,同樣象徵著一代新人「從傳統中創新」的努力,皆有斐然成就,值得讚佩。 十年有成的「雅音小集」,自七月廿日起,在國家戲劇院演出「紅綾恨」新劇,連演五天,場場客滿,可謂菊壇盛事。由此以觀國劇未來發展,再度驗證了「事在人為」的道理。演出者有精益求精的敬業精神,不斷追求進步,觀眾有熱烈反應,自在情理之中。印象中,郭小莊的戲,悲劇以「王魁負桂英」為壓卷之作,喜劇則「紅娘」最為精美。「再生緣」等反映出創新的著力,有時舊戲新編則瑕瑜互見,像「劉蘭芝與焦仲卿」,我覺得似乎反不及北平戲校「孔雀東南飛」的老本子。 這次演出的「紅綾恨」,比前此的幾部新戲更見出色。除了郭小莊自己和同台演員們的辛勤研練之外,我覺得編劇的王安祈女士應居首功。從觀眾的角度而言,每一個演員都是一種工具,一個有靈魂的工具;一齣戲整體的成功,基本上還是要有好的劇本。人能捧戲,戲亦捧人;所謂戲能捧人,就是劇本在一個合情入理的大間架上,又能讓演員有充分發揮。「紅綾恨」的成功,正是這大間架與演員之間良好配合的一個例證。 「紅綾恨」演的是明末崇禎皇帝的亡國恨史,而以帝女長平公主的婚姻作為推展整個悲劇的主軸。 明思宗崇禎是明朝的末代皇帝,少長深宮,不諳民間疾苦,雖有心力挽狂瀾而才智不足,繼位之初,內有流寇作亂,外有強敵崛起。但他寵信宦豎,偏聽小人,像袁廷煥等抗敵名將,都被他在「喜怒無常」的情況下誅戮殆盡,自毀長城。而他所親幸的權貴和宦官,一遇急難,或逃或降,他在臨死前還說:「朕非亡國之君,臣皆亡國之臣。」其實,他這掌握了升黜生殺大權的皇帝老哥,單祇是「無知人之明」這一條,「亡國之君」的罪名就逃避不了。 當時李自成作亂,荼毒中原,進兵京畿;被朝臣們倚為中興柱石的吳三桂,為了愛妻陳圓圓被虜,「衝冠一怒為紅顏」,竟不計守土之重,招引外敵,於是清兵得以長驅入關。流寇固然蕩平,大明江山也從此淪亡。 悲劇性的史實,往往就成為小說戲劇的好題材。同劇過去把這一段史實搬上舞台的,至少有兩齣,主演者當時的聲名,都在今日郭小莊之上。 一是鬚生高慶奎的「煤山恨」。煤山亦名景山,是北平故宮範圍內的小丘,也就是思宗以髮覆面、自縊殉國之所。高慶奎自演崇禎,有大段的反二簧,戲路與「逍遙津」裡的漢獻帝相近。 高慶奎是劉鴻聲的傳人,其唱腔以高亢激烈為主,與鬚生正統的譚派頗有出入。但他極盛時,與余叔岩、馬連良並稱為鬚生行裡的「三大賢」,其名貴可知。晚年體力衰減,際遇不佳,他的兒子高盛麟,是富連成科班出身的武生翹楚。 高慶奎去世多年,「煤山恨」似已失傳。 另一齣則更為有名,那就是梅蘭芳的「貞娥刺虎」。梅自演費貞娥,劉連榮的羅虎。這戲是照老本子,以崑腔為主,演出場數不多。 「紅綾恨」對於以上情節,都已吸收融匯,但主線是在長平公主身上。 長平公主史有其人,帝為其選婿,「將婚,以寇警暫停。城陷,帝入壽寧宮,主牽帝衣哭。帝曰,『汝何故生我家!』以劍揮砍之,斷左臂。」這位身遭家國淪亡之變的公主,在明亡後悒鬱而死。 但在許多稗官野史之中,這斷臂的公主流落江湖,大難不死,得遇異人,面壁修持,深研佛理,精通武功,潛身草野,不僅是武林共仰的宗師,而且是民間抗清復明的精神領袖。「獨臂神尼」的大名,自有許多行俠仗義、誅奸起義的故事可寫。此後如紅姑、甘鳳池等江南八俠,都算是她門下的後輩。這當然是出於小說家的「補償」心理,以帝女為中興再起的象徵。 「紅綾恨」取的是平實路線。她身經亂離,雖然沒有死於亂軍之中,但也並沒有在武學上自成一家的際遇。劇情的發展與史實大抵相合。它的戲劇性著重在明清交替之後的對立與衝突。興亡之際,暴露出人性的醜惡與堅貞。 全劇共分八場:「緣訂」、「寇讎」、「殺宮」、「忠憤」、「避禍」、「庵遇」、「哭殿」,和「花燭」。演足三個小時。 從開場的選將開始,就呈現了劇情內在的張力。公主彈箏,那「可憐荷鋤翁」一曲,歌哭當時戰亂流離之苦,是反映社會現實的藝術作品。公主雖然不出深宮,對於國破民窮的慘況,存有極深的同情。她認為作為駙馬候選人的周世顯(曹復永),不過是又一個攀龍附鳳、熱中利祿之徒;而身負長才、蒿目時艱的周世顯,對於皇家種種有失人心的作為,也有滿腹不平。他們之間的對白,針鋒相對,劇作者透過這兩個主要人物的心情,來刻畫所謂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的意境──而這種「通」是來自對國艱世危的關懷,並不是兒女之私。 他們的兩情相悅,是建立在某些共同信念之上。周世顯就是「可憐荷鋤翁」的作者,這是他們在風雨聲中突破暫時的誤解而能緣訂終身的關鍵。 李闖賊軍入城,宮廷告警,為小說裡的「過橋」,是一轉折。然後在宮中舉行婚禮,以紅綾作為愛結同心的惟一象徵。但這已是賊兵殺進宮廷的時候。崇禎(楊傳英)交代後事,手刃公主,太子走國,皇后自盡,崇禎派出迎敵的宦官,也已投降。崇禎便祇好到煤山上吊去了。楊傳英這一場表演是很稱職的。 未成年的太子走遊吳三桂軍中,這是政局再變的一線之望。但是,吳三桂迎清兵入關,明室遺臣紛紛降清;忠義之士原來對吳抱著莫大的期望,卻不料這中興柱石竟成了賣國的叛臣。淨角李國楨力戰不屈而死,代表著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」的最後奮戰──陳元正的那幾段唱腔,雖然著墨無多,卻充滿了陽剛之氣,使全劇生色不少。 長平公主的逃亡、遇救,都有極緊湊而合理的安排。郭小莊那一大段二簧慢板,「恍惚間依然是承歡膝前,只見那冷月無聲依窗欄」,唱出了思親愛國,情無以堪的悲慟──這是全劇精華。「杜鵑枝頭恨,血淚含悲啼」。從九重宮闕的繁華,淪落到荒郊草庵裡,忍辱偷生,這種身世之痛,當然超過了「鎖麟囊」的貧富突變和「竇娥冤」裡的屈抑沉冤,在個人的悲慘遭遇之上,更有亡國的沉痛。 所以,在「庵遇」的一場,劫後夫妻重見,那種「乍見翻疑案」的情景,刻畫得淋漓盡致。小莊的韻白:「心中已無兒女情,再回頭已似百年身。」有畫龍點睛之妙。應該說這就是全劇的「睛」。 「哭殿」是全劇高潮。長平與周世顯雙雙上殿,與清帝(朱陸豪)展開的詞辯,抑揚吞吐之間,極見功夫。演得好,本子寫得好。朱陸豪在這戲裡沒有機會展示他的武工,是一微憾;但他與長平之間的對話,有征服者故作寬容的「身段」,更有骨子裡輕蔑的一面。當他說「此一時,彼一時」,嚴詞拒絕開釋太子的時候,正是精簡而具體地說明了政治鬥爭,成王敗寇的無情。 清兵入關,初期都是假借漢人之力來收服人心。吳三桂引狼入室,而後文如范文程,武如洪承疇,都是靦顏事敵,效命新主的變節者。朝堂上遺臣三百,(戲中有的是剃光了頭冒充和尚以求避難,然後又戴上帽子來求官職的)。長平公主那一大段流水和哭腔,責罵那些叛國降臣,「廉恥何在?人心何存?」如果說戲劇的作用,是寓教化於娛樂之中,盡忠報國,是傳統的美德,也是中華民族善處憂患,仆而復起的一個主要力量。此中針砭,自有其時代意義。 不過,就明末的政局而論,上有朝廷昏瞶乖張,下有群臣貪鄙無恥,於是民生顛沛,百姓遭殃,已經到了離心離德的地步;所以內不足以平流寇,外不足以抗異族,不亡何待? 一旦山河變色、國土淪亡,覆巢之下,焉有完卵?亡國之痛,又豈止是三尺紅綾而已!這是看戲的人不可或忘的痛切教訓。 「紅綾恨」在十年有成的「雅音小集」而言,是一項新的突破,也是可喜的成就。 第一、劇本好,題材有分量,結構與演出的方式,都有推陳出新的佳構。情節鋪敘盡情合理,而又能扣緊觀眾的心弦,劇作者的心血功力,值得稱賞。 第二、「雅音」過去的劇目,大都以旦角和小生為主,不免略見單薄。此劇中生旦淨末丑各有表現,比較合乎傳統的要求。邊配角色也都很認真求好,這是使全劇顯得有「精神」的重要因素。 第三、國劇的布景,究竟應該抽象或具象,久有異同意見。此劇布景精美,極見慧心,第一場後宮中鼓箏的景物,接下去馬上換來接見周世顯那一幕,都很有氣魄。事前就說換景小有延擱,但在現場表演時,一切順遂。這樣的創新,觀眾不僅可以接受,而且是很欣賞的。 第四、近年各劇團對於演員服飾都相當考究。此劇中也都是煥然一新,不再墨守成規。長平最後「冠服上殿」的一場,小莊以珠冠素蟒出場,表情之中凸顯其帝女身分,設計很好。全白的宮妝以前似未見過。 以如此大的劇幅,其間可以斟酌損益之處,當然還是有的。哭殿那一場,小莊有三十句倒板轉流水和垛板,段落參差,聽起來吃力,雖有創新之美,難辭「花梢」之咎。刻意求新,固然值得讚賞,但還是要顧到整個劇情的要求,鄙意以為如果是用二簧散板式快三眼,或更有助於千山萬壑、奔流入海的悲憤之勢。 又第二場「寇讎」,起打似尚欠火熾。李闖入城,以管弦配樂,不足以顯示金鼓殺伐、兵荒馬亂的氣氛,似乎可再研究。 總體而言,「紅綾恨」是一齣站得住的好戲。當得起「國劇傳統的新生」這樣的讚詞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