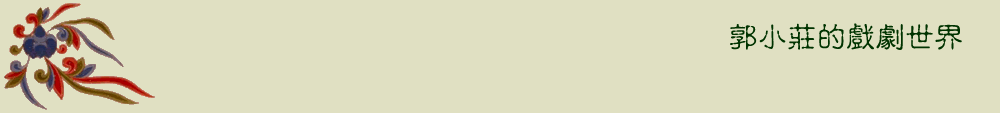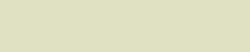傳統與創新的迴旋折衝之路
台灣京劇五十年
【王安祈】
約1999
本文對於台灣京劇的概況介紹,自民國三十八年(1949)國民政府遷台開始,直到世紀之交,共計五十年。這是本文的研究範圍,但並不是說京劇在台灣的歷史就只有五十年。政府遷台之前的一段戲劇歷史,在呂訴上《台灣電影戲劇史》一書開啟研究端緒之後,邱坤良《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(1895-1945)》以及徐亞湘《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》兩書可被視為研究成果最豐碩的代表*1,而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」於民國九十年(2001)將李坤城先生所蒐藏的台灣早期唱片精選製為光碟,出版為《聽見歷史的聲音1910∼1945台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》*2,則在文獻之外又對聲音資料作了鉤沈(其中台灣灌製的京劇唱段共有十二段)。由於這些研究已十分完整且深入,此處僅簡略引述要點,作為本文的前言開端。
台灣最早的京劇演出活動,根據連橫《雅言》一書的記載,始自光緒十七年(1891)*3。時任台灣布政使司的唐景崧為母祝壽,特地請上海班來台演出京調,這是台灣目前可考最早的京劇演出紀錄。不過因為這次演出屬於私人堂會性質,並未擴及民間,觀眾層面局限於少數特定對象,對台灣戲劇文化影響並不大。京劇活動真正的在台展開,必須要從日治時期算始。
日治初期台人因「本島(台灣)戲既不堪入目,內地(日本)戲尤非本島人之所嗜好」*4,所以引進距離台灣較近之福州徽班「三慶班」來台演出,隨後又有福州「祥陞班」受邀來台獻演,二班於台北、台南二地的演出皆大受觀眾歡迎。到1908年開始請上海京班來台,整個日治時代從1908年第一個來台演出的「上海官音男女班」開始,至1936年最後一個上海京班「天蟾大京班」離開台灣為止,近三十年間,計有五十個左右的上海京班在台巡演。中日戰爭爆發,日治時期上海京班的來台演出才劃上句點。
日治時期上海京班在台灣的活動雖然有起有落,但從以下幾個現象,可以看出京劇在台灣已埋下了根苗:本土京班的形成、本地京調票房的成立、藝妲的學習京調、京調唱片的大量發行,以及本地戲班的加演京劇。*5
來台做商業演出的還有福建、廣東等地的劇團,不過,上海京班佔其中絕大多數,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二,為台灣埋下京劇根苗的是上海京班,海派戲是日治時期台灣京劇的主要內涵。直到民國三十七年底(1948)顧正秋所率「顧劇團」來台,才突破海派戲範疇,全面展示京劇的各種藝術,為京劇在台奠定根基。
一、生命典型的樹立──顧正秋
顧正秋是民國三十七年底(1948)率團來台的,原本是應「永樂戲院」經理之邀來做為期一月的公演,但因觀眾反應熱烈所以臨時續約留了下來,沒想到這一留就真的落地生根了。就顧女士而言,來台推廣戲劇原是懵懵懂懂,然而,無心插柳,柳竟成蔭,顧劇團的永樂五年,開啟了台灣京劇史的扉頁。「顧劇團」的「永樂五年」(民國三十七年底至四十二年夏,1948-1953)在戲曲史上佔足了份量。
顧正秋有深厚的傳統師承基礎,但演唱時能以「發揮自我特徵」為前提,使得「師承」為己所用,許多唱段均能展現個人獨特風韻,贏得「顧派獨家唱法」之美稱。但是,對台灣京劇整體發展而言,最主要的意義仍在「傳統之接續與深耕厚植」。
顧正秋的藝術造詣,將京劇最美好的一面在台灣做了鮮明且長期的展示,而顧女士本身特殊的經歷與抉擇,更使得觀眾對她的為人增添幾許愛憐與尊敬。顧正秋三個字在臺灣的社會中儼然形成了某種象徵意義,這個名字代表的是藝術上難以超越的頂峰,更是家國劇變、人生旅程困頓周折之際的主要精神依恃。對許多人而言,顧正秋清潤的嗓音與獨特的唱法,早已潛入心靈底層進入永恆的記憶,而顧正秋所代表的京劇,也隨之植根於台灣土地。若為顧正秋做歷史定位,其實已超越傳統或創新的討論而進入「樹立生命典型」的境界了。
二、由一票難求到白頭低迷──軍中劇團由盛轉衰
顧劇團解散後,中堅份子分別輾轉進入「軍中劇團」成為主力,持續著深耕厚植的努力。
軍中劇團是在軍中康樂隊的基礎之上陸續成立的,幾乎網羅了當時在台的大部份名伶,而「小班」的學生也在往後十餘年內陸續長成,以徐露為代表的這批新血和王振祖先生私人創辦的「復興劇校」的學生一樣,純粹是在臺灣培育而成的戲曲人材。他們和大陸來台的資深名伶長期同台合作,共同為台灣的京劇舞台開創過一段絢爛時期。至少在七○年代初期以前,戲迷的人數還相當可觀,一票難求的現象隨時可見,而演員本身的藝術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。
當時的劇目多以傳統為主,這當然和政府遷台後整個文化甚至政治趨勢有密切關係。在這樣的觀念影響之下,「編演新戲」的風氣在很長的一段時期中並未被有效的帶動。大部份的新戲創作都展現在每年十月由國防部主辦的「國軍文藝金像獎」(即俗稱「競賽戲」)的編寫上了。由於競賽戲基本上是以「鼓舞國軍士氣」為前提,所以選擇題材時特別強調主題意識。近年來競賽戲承擔了許多社會上的負面批評,但至少就當時觀眾現場熱烈的反應來看,或許我們仍不宜以一句「政治干預戲曲」來為它做籠統的論斷。因為至少六○年代結束以前,國人的愛國精神還十分高漲,「反攻大陸」也還是明確的希望,因此當演員高歌著「為國拋家從無怨」「何日裡山河一統」之類的唱詞時,無論台上或台下的情緒都是同樣激動而真誠的。在時移勢變的今日,當我們回顧這段舞台演出史時,與其指責其藝術呈現不夠自由純淨,倒不如從「戲劇是社會某一面相的反映」這個角度來考量其時代意義。直到七○年代開始,社會發展漸趨多元,各種不同的思潮隱隱浮現後,競賽新戲的千篇一律才使人難以認同,而戲曲之與社會脫節的現象才也日益明顯。
當京劇與社會之脫節日益明顯時,許多有心人士也曾嘗試過多方面的努力。不過這些戲曲愛好者卻顯得熱心有餘卻缺乏策略,當他們在做「發揚國粹」的演說時,往往只停留在道德訴求的層面上,刻板地「指導」青年該從中學習忠孝綱常倫理精神,對於戲曲表演美學的特質又多偏重片面零碎的舉例介紹,而忽略了應從風格體系上做根本的提領。整個劇壇的風氣是老成嚴謹而缺乏生命活力的,台上的演員仍努力追摹著流派典範,整個劇場卻浮盪著「白頭舊識、共話當年、沉緬往事、憑弔餘韻」的低迷情調,對青年人而言,京劇是「應該值得尊重的國粹,但是我不懂,也不想弄懂」的不相干存在,在整個社會之中,京劇則像一個絕對擁有崇高地位,卻無法也不屑於進入任何現代文化藝術網路之中的尊貴骨董。崛起於民國六十七年(1978)「雅音小集」,首先改變的就是京劇前朝遺老的身份。
三、精緻藝術與菁英文化──「雅音」與「當代」為京劇轉型
使京劇的性格由「前一時代通俗文化在現今的殘存」轉化成為「現代新興精緻文化藝術」是「雅音小集」最主要的「轉型意義」。
由郭小莊女士成立的「雅音小集」,率先把國樂團以及現代劇場的專業人員引進了京劇的製作群中,這些「外行」或許把京劇搞得不純粹,但他們的參與不僅使京劇產生了質變,更因而激起了藝文界人士的參與感。京劇的演出不再只是上一代的消遣娛樂,它終於成為藝文界人士普遍關心的文化活動了。京劇與當代各類藝術之間突然變得關係密切,當代的戲劇(包括電視、電影、舞台劇等)開始逐步滲入京劇,京劇的「純度」開始減弱,傳統的表演技藝已不是劇評的標準,觀眾對戲的要求已明確地由「曲」而放大到「戲」的全部了。
這樣的作風雖然遭遇傳統界強力的反彈,但所幸是因緣際會地遇上了迎風順勢的七○年代(1970-)。七○年代不僅是台灣經濟起飛的時代,同時也是外交挫敗導致文化轉折的關鍵時刻,被西方文化殖民已久的台灣人民,開始思索「本國文化在世界中何以自處」,社會上「凝聚民族文化認同感」的強烈氛圍,具體表現在「雲門舞集」、「蘭陵劇坊」等當時崛起的藝文團體之上,《白蛇傳》、《烏盆記》、《荷珠配》是他們所選擇的內容,但是,在早已深受西方審美習慣所影響的台灣,雖然亟欲重新開始認識民族藝術,卻還沒有到達把「傳統」原樣照搬的地步,其間務必經過轉折調融,於是,西方的表演技巧(如「雲門舞集」的現代舞)、象喻內涵(如「蘭陵劇坊」對荷珠的新銓),乃至於西方劇場的秩序規律,和傳統相互結合,古老的藝術才可能登上大雅之堂為新生代觀眾所接受。「古老」與「前衛」似乎成了一體之兩面,而「傳統/現代」的關係是相反卻又相成的,京劇,也正處於這樣的關鍵時刻,當「雅音小集」以「傳統國劇的現代化」為標幟振臂一呼時,很自然地激起了年輕人探根尋源的熱情。
繼之而起的「當代傳奇劇場」,一方面將西方經典納入中國體系,一方面又欲蛻變傳統戲曲為新劇型,實驗性更強,菁英文化的趨勢甚於雅音之精緻。主要貢獻在打通了傳統與現代之道路,但京劇本位主義者,則嫌其有「置京劇於不顧」之心態。
比較明顯的例子是《奧瑞斯提亞》,這是由京劇演員、京劇作曲搬演的希臘悲劇,導演是美國著名「環境劇場」導演理查謝喜納,演出地點在大安森林公園。這齣戲雖有吳興國、魏海敏突破性的演出,也有作曲家李廣伯的精心設計,但是,整齣戲對於希臘名劇的解構新詮,幾乎全操縱在導演一人手上。在兩岸諸多創新劇作中,我們雖然都感受得到導演整體調度之功,也舉得出許多巧構精設的著名片段,但是導演的功能多止於把劇本「挺拔地搬上舞台」,很少有對原著劇本做大幅度的重新詮釋,而《奧》劇讓我們看到了導演對全劇整體精神的全盤操弄。原本莊嚴肅穆的悲劇,經他以「悲劇的悲愴→通俗劇的濫情→綜藝節目的騙局」三段式不同風格處理,把原著「民主」的真諦做了誇張的嘲弄。雖然演員、作曲、舞美在技術層面上都各有創意,但這些全都為導演一人的理念而服務,可說是集眾人之力共同體現謝喜納對於希臘悲劇的「解構」以及對於民主法庭的懷疑。這是完完全全的「導演中心」,比兩岸所有創新戲曲的做法都要全面。雖然有些學者不贊成導演的觀點理論,但無論如何他的觀點是藉著這齣戲清楚呈現了。只是,導演的興趣主要在自我理念的表達,至於「京劇」似乎不是他熟悉也不是他感興趣的所在。也就是說,京劇演員身上口裡豐厚的藝術根柢其實只為導演一人之理念而服務,至於京劇表演體系當如何豐盈或如何轉換,導演卻沒有太大興趣。
很明顯的,「雅音」的興趣在京劇本身的創新,「當代」的理念,則企圖由京劇之轉型導致蛻變形成另一種「新劇種」。新劇種的探索之途當然應該試闖,中國戲曲在崑、京之後該添新頁了,只是這項工作絕非一蹴可幾,也不是某一個劇團即能做到的。而在「當代」以前瞻的眼光蓄勢待發之際,整體台灣的文化思潮卻似乎有些轉向了。
四、文化議題與本土題材分別融入京劇──解嚴後的劇壇
九○年代「解嚴」之後,大陸劇團相繼登台,「大陸熱」對台灣劇壇的影響有新舊兩方面:
• (一)由於著名演員來台演出(有許多演員是流派創始人的嫡傳或後代),傳統的「流派藝術」再度受到重視,審美標準亦有回歸傳統的趨勢。
• (二)大陸半世紀「戲曲改革」的成果在台灣實際演出呈現,和台灣自行由民間劇團提出的創新觀念相結合,具體表現在「復興劇團」的幾齣新戲新風格之上。
同樣也在解嚴之後,台灣劇壇的評論風氣轉盛,新編戲引發了熱烈的討論,由於評論與創作之間的雙向關係足以視為觀察劇運發展之重要面向,我們可用「劇評現象」來觀察「復興劇團」的創新作品引發的風潮。
從《潘金蓮》、《美女涅槃記》、《阿Q正傳》與《羅生門》四齣戲的評論中,可以歸納出四項討論要點:
(一)「導演」的職能鮮明、成績出色。這點由《荒誕潘金蓮》兩個版本的比較即可清晰證明。魏明倫的川劇《荒誕潘金蓮》,由「復興」改為京劇形式演出(劇本也改了很多)三個月後,原創川劇團也由來台公演,同一劇目原創、改編二版相繼在臺演出,台灣的觀眾顯然對復興京劇版印象好得多。導演活潑以及運用象徵的手法受到一致好評,台灣製作的特色逐漸凸顯。
(二)女性心理的深入挖掘受到編導重視,傳統戲曲能結合台灣當前重要文化論述。不僅《荒誕潘金蓮》和《美女涅槃記》以女性為主,即使是《羅生門》也沒有忽略這項議題。
(三)文化批判的態度顛覆了傳統戲曲的教化本質。戲曲一向是被用來進行道德教化的宣傳機器,而《美女涅槃記》等劇卻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虛偽道德進行了猛烈的抨擊,因而為傳統戲曲的轉型在意識型態上提供了新基礎,嬉笑怒罵在此有著深遠的文化意義。
(四)台灣符碼的加入。《阿Q正傳》裡有歌仔戲「都馬調」、台灣民謠「草蜢弄雞公」與西皮二黃的結合,另外還穿插了台語念白以及「數板」中的台灣食物,劇場效果頗佳。而劇評界也提出:台灣符碼加入之後,符碼的內在意義(也就是「觀點視角」)是否也能深刻透現?也就是說:本土語言音樂風物的穿插融入,除了具備「打散京劇純度以跨越單一劇種」的目的之外,應該還應呈現「此時此刻台灣的製作對阿Q的新詮釋」。
(五)挑戰戲曲的性格塑造。無論是卑微的小人物阿Q或是以「人心乃難解之謎」為主題的《羅生門》,性格塑造都迥異於戲曲的善惡分明,而在面臨這項挑戰時,傳統京劇工作者更需要突破道德的防線,除了表演程式需要創新之外,內在的規範程式更需突破。
這樣的評論是極為有趣的,對話內容擴大了,不再只談:這種表演是馬派和麒派的兼容並蓄,這種唱法是京劇和梆子的聲腔融合,這種性格塑造是老生吸收了花臉……這些議題直探戲曲本質的極限,這些新戲所帶動的論述層面已突破了以往的京劇理論範疇。
而解嚴對整體社會更大的衝擊還不止於此,九○年代的「凝聚民族意識」較七○年代更深一層轉折,反映在京劇界,最鮮明的是「國立國光劇團」於創團之初即提出的「本土化」宣示。
民國八十四年(1995)軍中劇團解散重組為「國立國光劇團」時,象徵的是京劇從此回歸藝術、脫離軍政,而「國光」甫一成立即做出了「本土化」的宗旨宣示,代表的是京劇將從中原視角中掙脫,正式面對生存的土地、由衷擁抱鄉土。這層意義受到普遍的重視,相應而來的《台灣三部曲》三齣新編戲,便成為透視這項總原則實質內涵的具體例證。
去年春第一部曲《媽祖》演出之後,周慧玲在劇評會裡有極深刻的見解,她首先提出一寬廣的視角,企圖解脫此一口號可能引發的政治迷障:「本土化的意義不止台灣化」,其實應可突破「政治正確」的思慮而深化為「自生存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愛恨情仇中取材,傳遞現代人的心情處境」的藝術指示。因而,「本土化」和「現代化」並沒有什麼實質的差異,它們的內涵都是「藉京劇傳遞當前這塊土地上的人們的情感思想」。這樣的說法,為「京劇本土化」提供了非常周延而且是純藝術性的解釋,如果《媽祖》的劇本能掌握這個關鍵,能正視台灣社會近年來「在宗教與理性的對抗中」的自我迷失,「本土化」理念和藝術之間,便能有深刻結合。
經過一段時間的琢磨,國光終於在第三部曲《廖添丁》裡展現了導演和演員的朝氣與活力,完全擺脫了保守的印象。全劇的創新並不在於加入了「台語、武士刀、和服」(大陸的現代戲在這方面作了五十年的嘗試,我們怎能期待於一齣戲裡解決所有的尷尬?),成功之處盡在於「舞臺調度靈活、武技身段設計精彩、整體節奏流暢(尤其上半場)」,如果布景設計能再靈活或簡易一些,導演或許更能揮灑得開。不過,劇本的問題還是根本,這是個很「小品」的劇本,雖然不乏精彩之處,但是,情節份量單薄了些,尤其下半場素材過於簡單,只好加入大段的唱,而這次的作曲不夠靈活,許多腔很傳統,反而拖緩了節奏,好在朱陸豪和朱勝麗的唱工表現突飛猛進,仍能吸引觀眾。儘管「義賊?小偷?」的討論空間不大,但本土化終究邁過了「題材本土化」的初步階段而能在藝術上做出嘗試了。
尾聲
半世紀來,台灣京劇歷經了幾番風雨,由繼承傳統到銳意創新、由被尊為國劇到劇團合併、由追求東西方藝術碰撞的火花到回歸本土,以及大陸劇團來台後由備受衝擊到重新自我定位等等,這些不只是政治環境的轉換,更是隨著文化變遷而逐步形成的藝術特質。五十年來的經驗,本文試圖在有限的文字中稍做總結,希望能為下一世紀的戲曲新局提供經驗。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*1 呂訴上《台灣電影戲劇史》,台北:銀華出版社,1961年。邱坤良《日治時期台灣戲劇之研究1895-1945》,台北: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,1992年。徐亞湘《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》,台北:南天書局,2000年。
*2 《聽到台灣歷史的聲音──1910∼1945台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》,台北: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,2000年。
*3 連橫《雅言》,《台灣文獻叢刊》第166種,頁35。關於京劇來台之始的考察,一般都上推至劉銘傳任台灣巡府時,根據徐亞湘研究,劉銘傳所請的其實是福州的徽戲,詳見《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》,台北:南天書局,2000年,頁10。
*4 1906年8月28日《漢文台灣日日新報》,本段資料及觀點引自徐亞湘《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》,台北:南天書局,2000年,13頁。
*5 徐亞湘〈日治時期台灣京劇之發展面向及文化意義〉,收入《聽到台灣歷史的聲音-1910∼1945台灣戲曲唱片原音重現》,頁37至39。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