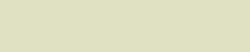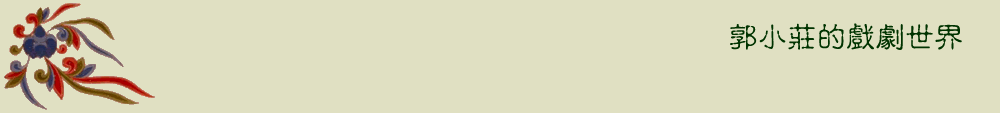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長闊高深師生情(上) 今年五月二日,俞老師逝世卅周年,也是他老人家百歲冥誕,藝文界推出連串的紀念活動,曾力邀我演出當年俞老師特別為我編寫的《王魁負桂英》。 十年沒有演出了,面對這項邀約,內心百感交集,往事一幕幕在腦海中重現,平靜多年的心湖,也幾度翻攪,我何嘗不想讓俞老師在天之靈,看看當年不識愁滋味的少女,歷經卅年人生淬煉後,對他的作品是否有更深層的體悟?但是,我的內心是掙扎的,我一再自問:這是紀念俞老師最好的方式嗎? 如果俞老師在世,他會希望我怎麼做?這是我失去俞老師的帶領後,每當遇到問題、挫折時的第一個反應。靜下心來,從過往俞老師的教導中,我會找到答案…… 那年,我十五歲,一個剛從大鵬劇校畢業,受完傳統戲劇基礎訓練的小女孩,長年生活在軍事化管理的劇團,每天的功課就是練功、吊嗓、排戲,那時的我,對同齡女孩進大學優遊浩瀚書海的學生生活更是嚮往不已。 某個機緣下,我利用排練的空檔,怯生生地走進淡江文理學院(現在的淡江大學)城區部,在俞老師開的詞曲課堂中,選了最後一排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坐下,我想:「沒有人會注意到我的。」 下課鐘響前,俞老師突然冒出一句:「今天班上多了一張陌生的臉孔哦!」霎時,全班目光都投向我,舞台上唱作唸打應付裕如的經驗,在這樣的場合中,畢竟派不上用場,突然成了大家的焦點,難免露出小女孩的窘態,俞老師親切地問我叫什麼名字,「郭小莊。」名字一報,俞老師笑容可掬地說:「大鵬劇校的郭小莊?哦,我看過你的演出。」簡單的一問一答,陡然拉近了我和俞老師間的距離,而且是那麼自然。 上課一段時間後,俞老師問我:「願不願意到家裡來聽課?」就這樣,每周三、日,我固定到俞府上課,結下了往後十年的師生情緣。 回想當時俞老師桃李滿天下,仰慕他學養,欲親炙大師丰采、聆聽教誨的才俊之士何其之多,我何其有幸,能投入他的門下受教,確實受寵若驚。與俞老師這段師生緣曾是菊壇一段佳話,我不敢以千里馬自居,但俞老師在藝文界素有「伯樂」之名,當時的我,在俞老師的眼中應該是一塊值得雕琢的璞玉吧! ● 到俞老師家中「上課」是一大享受,沒有課本、沒有講義,當然也沒有考試,一切信手拈來,他的一言一行、一舉一動,都是我取之不盡的「活」教材,十年來,他牽著我的手,一步一腳印,從生活中指引我「走一條自己的路」,在踏上這條「不歸路」前,他已為我打點好必備的行囊了。 周日午後,植物園荷花池畔、新公園的老樹下,或是榮星花園綠草地上,俞老師、師母和我三人偕行,或漫步花叢,或倚欄閒話,先由我述說近來演出工作,再由俞老師教讀詩詞曲賦,甚至西洋戲劇思想,師母一旁伴讀,那段時光,對我而言,真是一場豐盛的知識饗宴。 有一回,楊柳樹下讀詩詞,俞老師對我說:「藝術最重意境,當你口中唱著楊柳,舉手投足乃至眼神中,都要呈現出楊柳的風韻神態。」這對我日後的表演,是多麼重要的啟迪呀! 結束鳥語花香中的課程,俞老師和師母就帶著我品嘗各種美食,有中餐也有西餐,餐桌上,俞老師從生活禮儀談到藝人素養,俞老師嘗言:「身為中國讀書人和藝術家,最重要的就是那股氣質,一種高雅脫俗又溫柔敦厚的氣質。」 當時年紀小,只覺得和俞老師、俞師母遍嘗美食是件快樂又期待的事。如今才深深體會俞老師對我用心之深,他透過生活禮儀,教我從飲食中體會傳統文化之美、藝術之美。走過人生風風雨雨,更能體會俞老師對我細心扎實的教導,是他要我從一個國劇「演員」,往全方位「藝術家」境界邁進的基本訓練。 ● 八歲進入大鵬劇校,所接受的教育與訓練就是「服從」,老師怎麼教,我就怎麼做,養成我「不提問題,只聽不說」的學習方式,俞老師總是親切地鼓勵我,不要只會「搖頭、點頭、微笑」,他說:「藝術家要有靈性,必先會思考,發現疑問、找出解決的方法,才能讓術業精進。」 追隨俞老師的十年,正值青少年階段,溫文儒雅的俞老師,讓我學會開口問,或許比教會我「靜」的功夫要容易,俞老師除了要求我靜靜地聽、靜靜地記,更要靜靜地想,也就是「靜心」,唯有如此才能正確地思考,隨著年齡增長,我漸漸悟出,「靜」才能由內而外展現從容、自在、優雅的氣度儀態。 俞老師對我的教導是全面的,除了個人氣質的變化、心性的修鍊外,對我的藝術事業更是親力親為,一方面為我編寫新戲,一方面為我改寫傳統小戲,先後更介紹顧正秋、趙仲安、呂寶棻、李香芬、馬述賢、白玉薇、梁秀娟等各派代表性的名師傳授我各派精華,領略各派之美,更重要的是,他叮嚀我「千萬不要拜師」。 後來我逐漸明白俞老師的用意,他希望我充實外在演出的條件,再加上內在氣質修養,集各派優點後,等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,水到渠成,我可以自創符合時代的新流派,當時他沒有明言,只不過是時機未成熟,也不想讓我承受過重的壓力。 (上)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