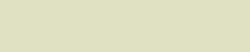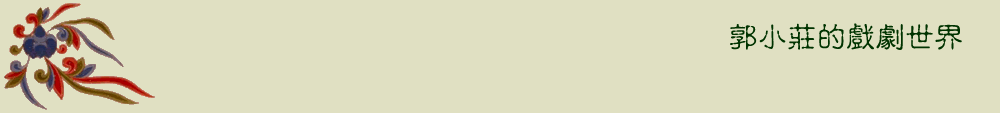
悼俞大綱老師 星期六,難得在報告和考試中緩過一口氣,拿出紙筆來給俞老師寫信,談最近在談的問題:怎樣就舞台、表演、劇場來寫一部中國戲劇史。朋友打電話來。「有一件事情我想妳應該知道,俞大綱先生去世了。」「妳在說什麼?」我問。朋友再重覆一次。「我前天還接到俞老師的信,我現在正在寫回信。」我說。 然而我知道這一切是真的,只時間在人世間的許多事情上開了很大的玩笑。我看著手裏寫一半的信,隔著太平洋,隔了七天信件來往,接到俞老師最後一封信時,老師已不在人間,而遲了一個禮拜才知道消息,我卻正在寫一封無法投遞的信。 去年聖誕節回台灣,見到老師時,卻必得發現老師蒼老了。出國兩年,對我來說如同煙雲,對上年紀的老師,卻分分秒秒都是歲月。 只俞老師還如同兩年前一樣健談,我以在此地剛學來的一點戲劇知識,同俞老師有了一場自認識近五年來最深切的談話。俞老師提及他有許多新的看法,比如過去以中國方型舞台與農田有密切的關聯,現在覺得還可以推得更早到殷商。要探求巫者與戲劇的關聯,就必需對人類學有相當知識。然後俞老師要我選些人類學的課,回去後他要指導我寫這方面的文章。 俞老師身體不好,沒法作刻板的學術研究,但一些觀點、看法,卻有極深遠的意義,我當時的高興當然不用說。可是,因著我實在很在意俞老師對林懷民、奚淞等人那般的寄以重望,心中有點酸溜溜的,我說林懷民等人也可以作這些事,俞老師說,他們是很聰明,可是畢竟不是學戲劇的,缺乏這方面的訓練。 直到此刻,淚眼模糊的來寫這篇文章,我都還記得那時候那種滿足的喜涗,那種覺得被委以重任的使命感。之後,我逢人就提及俞老師要指導我寫論文的事情,當然都同林懷民、奚淞說了。現在回想,當時實在孩子氣,可是,也只因為他是俞老師,我才會如此希望可以在他面前是最好的。 回去一個月,臨出前來的深夜打電話辭行時,我告訴俞老師,我也許就在國外結婚了,不知何時再回來,可是同時我又十分困擾,因為我父母親都希望我畢業後早日回來。俞老師在電話裏笑著開朗的說,妳父母希望妳回來,老師也希望妳回來,就回來了。又說,他寧可我是「文姬歸漢」而不是去「昭君和番」。 今天一整天裏,我片片斷斷的總記起這些瑣細的小事,還有就是想著下一次回台灣,不能再到館前街老師的辦公室見到老師,聽老師暢談古今中外,心語泛起難當的淒惶。 七二年暑假姊姊施叔青自紐約回國,想著手研究平劇。因著姊姊的關係,我得以認得俞老師。之後,姊姊到俞老師的辦公室上課,我常跟著去,聽一個真正讀書人暢談中國文、史、戲劇。俞老師的學識、胸襟、氣度、觀點,無一不令我深深折服。在知道俞老師因身體不好不能將這些觀點自己寫成文章後,那時候我就想,應該帶個錄音機,把俞老師的談話錄下來,再作整理。我同俞老師提及,老師笑著說,要作談話錄音,他也得有系統的放進相關材料,不能像普通談話,興之所至說到那裏就是那裏。之後,我忙著出國,考托福,僅只作成一篇訪問。總想回去後,自己有些戲劇方面的概念,再好好以問答的方式,錄下俞老師的觀點、見解,沒想到卻再沒有機會了。 然而如果這一切都是天數,天意要俞老師得如此突然的離開我們,我多少還是暗自慶幸著,至少我在上個聖誕節還回去,還得以再見到老師,上天畢竟眷憐作學生的我們,不至使兩年前的一別就成永訣。 朋友高全之遠自東部打電話來,要告訴我這事,他說,我以前老同他提俞老師如何又如何,恐伯我會很傷心,然後全之建議我寫一篇文章紀念俞老師,我說我會寫,只不知寫出來會是什麼樣子,能表達出多少我心中的哀慟。 先勇從南加州打電話來,我告訴了他,先勇連說惋惜,他還正想明年回台與老師好好學平劇。 我深深覺得的,過世了的不只是俞老師,而是一種風範,一種優良的傳統精神,一個古老文化的光輝。我止不住要想,來到一個陌生的異域,受到在台灣決想不到會有的苦惱,為的是希望能學習西方劇場,好有天回去,能在俞老師的指導下在平劇方面作研究,來保存這傳統戲劇的命脈。而如今,有誰可以去請問諸多的問題,暢談種種瑣事、天下、人生。也許我應該學習人們會說的,俞老師雖逝去了,我們更應該努力,好繼承老師在文化、戲劇的未完成的遺命。可是,為什麼我覺得這樣的茫然,這樣的不知何處可以依歸。 |